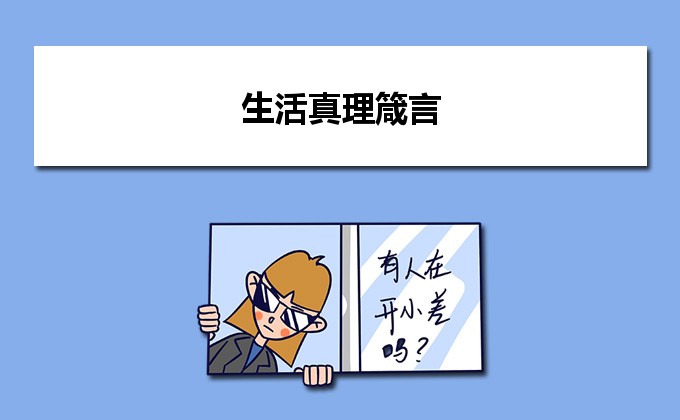人生在世,主觀上追求什么,就能從根本上決定一生的命運(yùn)。追求功名利祿的人,整天考慮的是他人對(duì)自己如何如何評(píng)論,必然活得累。自覺(jué)追求淡然恬靜的人,自然是榮辱毀譽(yù)不上心,按照自己的原則做人,做個(gè)古人所說(shuō)的“沒(méi)事漢,清閑人”。
個(gè)人在與社會(huì)、與群體相處的時(shí)候要和諧,盡量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,必要時(shí)甚至需要達(dá)到忘我的境界。但是,在自然之“我”與精神之“我”這對(duì)關(guān)系中,又應(yīng)強(qiáng)調(diào)后者:物質(zhì)生活清貧,精神生活卻應(yīng)富有。不管外界有多少有形無(wú)形的枷鎖,精神意志卻是自由的,“澤雉十步一喙,百步一飲,不蘄畜平樊中,神雖王,不善也”。山雞寧愿走十步或百步去尋到飲食,也不愿被關(guān)在籠子里做一只家雞;帝王雖然神圣,卻也沒(méi)有什么好的。這一點(diǎn),與西方的“存在主義”代表人物薩特似乎不謀而合。薩特在他的《蒼蠅》一劇中,借眾神之神朱庇特之口說(shuō):“神與國(guó)王都有痛苦的秘密,那就是——人類是自由的。”
“沒(méi)事漢,清閑人”不是無(wú)所事事,游手好閑者,而是精神自由的人,自由是寶貴財(cái)富。誠(chéng)如盧梭所說(shuō):“在所有的一切財(cái)富中最為可貴的不是權(quán)威而是自由,真正自由的人,只想他能夠得到的東西,只做他喜歡做的事情。”“放棄自己的自由,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,放棄人的權(quán)利,甚至于放棄自己的義務(wù)。”當(dāng)然,自由不是隨心所欲,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,有規(guī)則的,所謂“絕對(duì)的自由世界”純屬子虛烏有。
說(shuō)到底,自由就是順心盡興,但能順心盡興不是酒色財(cái)氣,吃喝嫖賭,而是有追求,不貪心,心性不可太盛,要奉獻(xiàn),但不虧心。要順和,但不違心,不同流合污。所謂有追求,不貪心,心性不可太盛,就是說(shuō),人生無(wú)論宏大的還是微小的,總要或總在追求什么,完全渾渾然無(wú)所求的人幾乎沒(méi)有。人要生存,要生活,就要有一定的物質(zhì)保證,以滿足起碼的生存需求。適當(dāng)?shù)奈镔|(zhì)追求也是天經(jīng)地義,無(wú)可厚非的。即使功名利祿,只要是付出所得,似乎也應(yīng)受之無(wú)愧。但若對(duì)于這些東西的需求,變成無(wú)止境的追求,并以此作為人格追求,價(jià)值追求,必然會(huì)貪心不足蛇吞象。即使一次評(píng)職稱,一次調(diào)級(jí),一次提干沒(méi)能滿足,甚至其中有明顯不公,也不可耿耿于懷,傷心勞神而窮追不放,甚至于放肆撒潑。這樣既無(wú)面子,又不宜養(yǎng)生。
要奉獻(xiàn),但不虧心。就是說(shuō),奉獻(xiàn)作為一種社會(huì)公德,倫理道德精神,它本身是高尚的,也是每個(gè)凡人或多或少可以做到的,所以不僅社會(huì)應(yīng)提倡這種精神,作為個(gè)人道德修養(yǎng),乃至于養(yǎng)生,都可努力去做。
與人相處得理時(shí),別咬住不放,得饒人處且饒人,尤其那些非原則的小事不要太認(rèn)真兒,鬧得不歡而散。如此日久天長(zhǎng),就成為“有人緣”的好人。但是生活是復(fù)雜的,處處有矛盾,事事有原則。
經(jīng)驗(yàn)告訴我們,心愿與現(xiàn)實(shí)常常陰差陽(yáng)錯(cuò),或歪打正著。你想當(dāng)演員,各種因素卻同時(shí)把你定在工人的位置上,成不了“星”還得鉆地溝。但只要肯努力,抱定希望,不斷充實(shí)自己,“是金子早晚會(huì)發(fā)光”,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只要“不死心”,精誠(chéng)所至,金石為開(kāi),最起碼也落個(gè)精神充實(shí)自由,在精神世界里汪洋恣肆、自由騰飛。
還是盧梭說(shuō)得對(duì):“人的自由并不僅僅是在于做他愿意做的事,而在于能夠做他不愿做的事。”這里所說(shuō)的自由,主要是指人的自我精神的自由而非行為的不自由。正是出于義務(wù)和責(zé)任需要,精神的自由雖受客觀制約,但它相對(duì)行為自由擁有更大的天地,更遼闊遙遠(yuǎn)的時(shí)空。